青海新聞網·江源新聞客戶端訊(記者 陳郁 報道)仲夏的高原演兵場,海拔近3000米的山脊線被勁風撕開一道口子。數架無人機突然從山后躍起,煙霧彈在峽谷間炸開灰白色屏障,電磁干擾波如無形利刃切割著空氣——第76集團軍某旅紅軍營營長張燦燦手持望遠鏡,在風沙中緊盯戰場態勢,沙啞的指令通過電臺穿透硝煙:“左翼突擊隊,沿無人機開辟通道突入!”
在這場戰術演練中,這位有著23年軍齡的高原老兵獻給強軍事業又一份答卷。2025年,張燦燦被中央宣傳部、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授予“最美新時代革命軍人”稱號,成為全軍官兵眼中“鐵心向黨、奮斗強軍”的鮮活注腳。

紅軍傳人的“硬骨頭”
“把血痂和木刺粘在一起的手套摘下來時,能看到掌心嵌著紅的血、黑的泥、黃的草屑。”新兵連班長至今記得,2002年那個隆冬,剛從河南夏邑入伍的張燦燦,總在天未亮時就扎著10公斤沙背心沖向結冰的獨木橋。在“夜老虎連”這座浸潤著紅軍血脈的熔爐里,“當兵不習武,不算盡義務;武藝練不精,不算合格兵”的標語,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信條。
2008年3月的高原障礙比武,鵝毛大雪讓2米深坑的邊緣結上一層冰殼。張燦燦的作戰靴剛踩上去就打滑,整個人重重栽入坑底,膝蓋撞上凍土的瞬間,劇痛讓他眼前發黑。“沖啊!”戰友的吶喊像火種點燃了他的斗志,他顫抖著抓牢坑沿,血痕在雪地上拖出蜿蜒的紅痕,最終以2分50秒的成績打破紀錄,比原紀錄快了整整3秒。“那一刻,我才敢說自己配得上‘紅軍傳人’這四個字。”他后來在日記里寫道。
同年5月,汶川大地震的余波未平,時任代理排長的張燦燦帶著22名戰士奔赴甘肅隴南災區。在一棟傾斜的危房里,老鄉哭喊著“血汗錢埋在底下”,他當即跪爬進搖搖欲墜的房梁下,徒手刨開碎磚斷木。10個小時的連續作業,戰士們的迷彩服被粉塵和汗水浸透成硬殼,終于從廢墟中捧出那沓帶著體溫的現金。老鄉拉著他的手往屋里拽,灶臺上的鐵鍋冒著熱氣,他卻笑著敬禮:“紅軍的規矩,不拿群眾一針一線。”
這種刻入基因的堅守,讓他在一次次考驗中挺膺而出。抗震救災榮立二等功、跨區機動任務中帶領連隊創破3項紀錄、合成旅改革時啃下多兵種協同硬骨頭……從戰士到營長,他的成長軌跡上,刻滿了“一心向黨、一意謀戰”的紅色印記。
轉型路上的“探路者”
“步兵連長玩不轉鐵疙瘩!”2014年,當張燦燦從步兵排直接被提拔為炮兵連連長時,老兵的嘀咕像塊石頭壓在他心頭。第一次組織迫擊炮集訓,他下達的口令磕磕絆絆,訓練標兵譚林林的竊笑讓他臉頰發燙。
那晚,炮陣地的探照燈亮到后半夜。張燦燦把射表貼在床頭,睡著時夢話都在背“射程修正量”,白天就追著老士官問操作細節,手掌被炮閂磨出的繭子疊了一層又一層。一個月后的實彈射擊,他親手操炮打出首發命中、全連滿堂彩的成績,譚林林紅著臉遞上一瓶礦泉水:“連長,我服了!”
2017年部隊改革整編,張燦燦又站在了轉型的風口。面對步兵、火力、通信等多兵種協同的新課題,他把專業教材翻得卷了邊,封皮磨破了就用膠帶粘好,筆記寫滿12個筆記本。在零下20攝氏度的高原駐訓場,他帶著官兵練夜間協同,電臺里的呼號與寒風交織,指北針的指針在凍僵的手指間微微顫抖。當實兵演習中多兵種如臂使指般突破防線時,導演部評價:“這支部隊打出了合成的‘精氣神’。”
無人智能技術浪潮襲來時,40歲的張燦燦再次清零自己。列兵張津浩遞來無人機遙控器的那天,他笨手笨腳的操作讓無人機在半空畫著歪歪扭扭的弧線,戰士們的笑聲里沒有嘲諷,只有親切。“我得向你們學!”他誠懇地說。很快,學習室的燈徹夜長明,官兵們圍著圖紙爭論,自研的無人裝備零配件相繼問世。如今,這個營已有一大批無人機操作手,“智能+”訓練模式在全軍推廣。
高原練兵的“排頭兵”
“張營長的迷彩服,永遠帶著股雪水和柴油的混合味。”這是戰士們的共識。在高原駐扎23年,風沙在他臉上刻下深深的溝壑,指甲縫里總嵌著洗不凈的泥垢,可他帶隊創下的紀錄比軍功章更耀眼。梳理20多條高原高寒練兵經驗,攻克10余項戰訓難題,某新型火炮在雪線的射表參數填補空白。
一次駐訓,他望著連綿的山體頓悟:“未來戰場可能在地下!”帶領官兵構設綜合掩蔽工事的日子里,他鉆進狹窄的坑道檢查結構,安全帽撞在鋼筋上咚咚作響。數月后,一座功能齊備的地下工事亮相,成為兄弟單位觀摩的標桿。“預設最難的情景,才能打贏明天的戰爭。”這是他給戰士們最常說的一句話。
2025年夏日深夜,張燦燦的辦公室仍亮著燈。地圖上的紅箭頭從高原指向更多未知地域,桌上攤著的訓練手冊寫滿批注。“打好建軍一百年奮斗目標攻堅戰,我們的腳步得再快些。”他對參謀們說,窗外的月光灑在他肩頭,像給這條進擊之路鍍上了一層銀輝。
從“夜老虎連”的新兵到合成營的營長,從鋼槍實彈到智能裝備,張燦燦在風雪高原寫下的,不僅是一個軍人的成長史詩,更是一支軍隊向強而行的時代答卷。當晨曦再次照亮演兵場時,他又帶著官兵沖向新的目標——那背影,正如他常說的:“紅軍傳人,永遠在沖鋒的路上。”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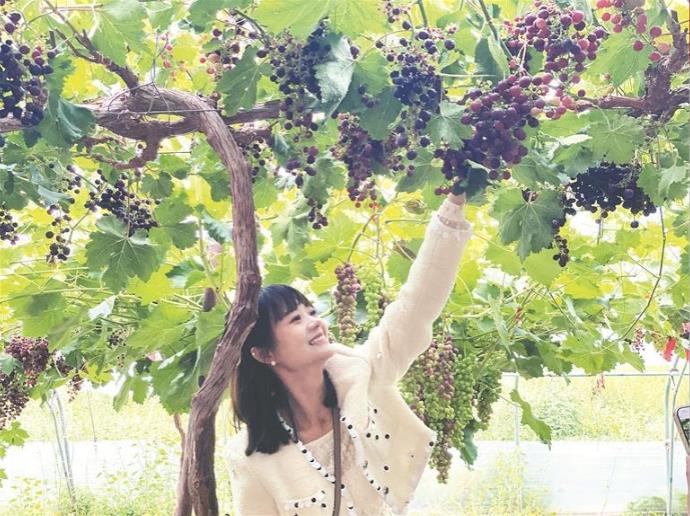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})
})
})
})